
■王婧 [杏悦娱乐法律文明史研究院研究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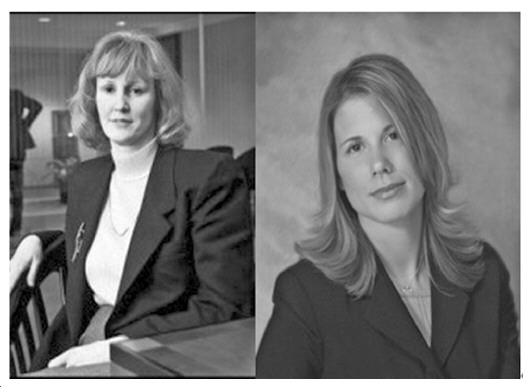
▲ 格魯特案和格拉茨案的兩位當事人:格魯特(左)與格拉茨(右)
教育平等事關起點平等
在現代社會中🫸🏿,由於高等教育對於普通公民的素養提升和職業選擇有更為重大與直接的影響🚴,其在招生錄取方面的平等對於起點平等的意義尤甚,但在教育資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衡的情況下,高等教育錄取標準的選擇卻面臨著兩難的境地🦪:如果貫徹形式平等原則,則應該按照統一標準,由此可能會固化甚至擴大既有的不平等;如果為了糾正既有的不平等而優待弱勢群體——這裏弱勢可能是經濟意義上的,也可能涉及種族𓀉、民族🧎🏻♀️➡️、性別、宗教或國別上的少數——則有助於實現實質平等,但卻可能讓統一標準之下能夠被錄取的非弱勢群體成員喪失教育的機會🕴🏻,引起逆向歧視。
格魯特案和格拉茨案
2002年,逆向歧視的難題擺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面前,一下子就是兩個案件,而且兩個案件原告都是密歇根州的白人居民,被告都是密歇根大學。1995年,原告格魯特申請進入密歇根大學法學院學習。法學院的招生政策規定,為了實現學生“多元化”,要錄取“關鍵數量”的少數族裔學生以保證在學生中形成有意義數量的代表,格魯特的申請被拒絕,她將原因歸結為:法學院將“種族”視為錄取的一個主要因素,且在沒有證明運用這種因素正當性的前提下,給予少數群體申請人比同等條件下的非少數群體申請人更大的錄取機會。另一案件的原告格拉茨和哈馬馳有著類似的遭遇,兩人分別在1995年和1997年申請進入密歇根大學文學、科學和藝術學院,結果遭到拒絕,兩人同樣認為,申請失敗是因為該院的一項招生政策: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族裔申請人可以在本科錄取所需的100分中自動加20分🥔。深感委屈的格魯特與格拉茨等人訴之於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捍衛自己的利益。這條通過於1868年的修正案規定,任何州均不得製定和實施法律“拒絕給予其司法管轄下之任何人以平等的法律保護”☆✔️。數年努力之後,她們終於成功地將案件上訴至最高法院。
作為憲法訴訟,格魯特與格拉茨等人質疑的不僅是招生政策,而是指向了整個糾偏行動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是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重要成果,旨在通過法律與政策在教育、就業🫱、商業等領域給予少數團體成員以優待,以糾正因為奴隸製度以及種族隔離所造成的美國社會對於黑人等少數族裔根深蒂固的歧視。直到1978年的巴基案,鮑威爾大法官才首次明確了最高法院處理糾偏行動的基本價值立場:首先,認可在錄取過程中考慮種族因素,這種考慮並非是為了糾正過去的歧視,因為這會使得無辜的第三者遭受不必要的負擔,而是為了在高等教育領域內“實現一個多元化的學生團體”,這種多元化是第一修正案推論出的“學術自由”所要求的;其次,種族的考量要“嚴格限定”,它“僅僅是一個大學在達到多樣化學生群體目標過程中可以恰當考慮的因素中的一個”。
在格魯特案中,投出關鍵票的奧康納大法官從教育的使命出發,發展了鮑威爾大法官的“多元化”法理:教育是形成專業技能,養成公民責任和領導力的一種手段,可以讓學生為日益多元化的勞動者和社會做準備,有助於形成多元化的軍隊以及國家領導人群體🔣。換言之,要讓少數群體有機會參與到民主決策的程序,疏通種族等級製度的政治變革渠道,這樣的解釋也為格拉茨案的多數意見認可🧙♀️。奧康納還明確了對種族優待的嚴格審查標準:出於迫切政府利益的目的和嚴格限定的手段。據此,密歇根大學法院在促進學生多樣性上有著“迫切的利益”,且法學院的優待錄取計劃在各個申請人的基礎上考慮了很多其他的因素,是“嚴格限定的”;而LSA自動加20分使得“種族因素”對每一個最低限度合格的、且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數申請人都是決定性的,而不是“個人化的”考量,不屬於“嚴格限定”。2003年6月23日,最高法院裁定👩🏼🍳:格魯特案的種族優待方案符合憲法,格拉茨案的方案違反憲法。
推行教育平等的奧義
類似的案由,相反的結果👂🏽,爭論未息:糾偏行動會讓所有受優待的人都背負上“不值得錄取”的汙名,會引發被逆向歧視的公民的怨恨🏔;嚴格限定是否對量化的優待過分嚴苛,對非量化的權衡又過分寬容等🙎♀️。眾多的質疑或許也能夠解釋為何最高法院沒有對糾偏行動是否違背平等保護給出一般性的憲法判斷,而是從功能和後果出發進行個案認定,有學者直言,糾偏行動的正當性問題應該通過民主而不是司法方式加以解決,但無論民主與司法,都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應該是讓每個公民在事關自身重大利益的問題上發出自己的聲音,即使結果並非如己所願,而這,或許才是現代社會推行教育平等抑或糾偏行動真正的奧義所在。
(來源於《法製日報》2016年12月07日)
